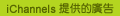第2章
一日將盡,彎彎的新月,上了枝頭。
熱瑟的清水,嘩啦嘩啦的從牆上的石虎口中流出,淌入寬廣的浴池裡。
這池子很大,長寬都數十大尺,足足能讓五個大男人在裡頭躺平。
浴池旁的燈火穩定地在琉璃罩裡散發著溫暖的光芒。
蒸騰的熱氣,充滿一室,教澡堂裡的事物忽隱忽現,瞧不太真切,但依然能隱約看見,一名體魄強健的男子半坐仰躺在浴池的最深處。
他雙手交疊在結實的腹部上,的身體泡在熱水之中,仰著的臉半覆著微溫的濕毛巾,只露出了口鼻。
的水,讓男人一點一滴的放鬆了下來。
當四下皆無人蹤,疲倦直到此時,方略微顯露出來。
水波蕩漾著,圍繞身旁。
恍惚中,似回到從前過往,聽到了嬌嫩的語音輕響。
貨分為三等,十合為一升,十升為一斗,十斗為一斛……
「阿靜、阿靜,我念的對不對?」
「嗯。」
「你有在聽嗎?」
「貨分為三等,十合為一升,十升為一斗,十斗為一斛。」
大男孩張嘴淡淡的重複之前入了耳的話。
春的夜,風微涼,淡淡花飄香。
一燈如豆,將桌案書冊照亮。
「你在看什麼?」
小小的腦袋瓜,晃了過來,好奇的趴在男孩前方,眨巴著烏黑的大眼問。
「孫子算經。」他頭也不抬的回答。
見他看得那麼認真,她拋下了前些時日他抄寫的宣紙,歪著頭瞧他身前那本書冊,一頭烏黑長發垂落幾許,她忍不住自顧自把看到的字念了出來。
「九九八十一,自相乘,得幾何?答曰:六千五百六十一……」唸到一半,她擰起小小的眉頭,伸出手指指著那個很多筆劃的字問:「這個字怎麼念?」
他瞄也不瞄,直答道:「術。」
「樹?柳樹的樹嗎?」她瞅著他再問。
「算術的術,但和柳樹的樹是同樣的音。」他說。
她點點頭,慢慢的繼續念:「術曰:重置其位,以上八呼下八,八八六十四,即下六千四百於中位。以上八呼下一,一八如八,即於中位下八十。退下位一等,收上位八十。以上位一呼下八,一八如八,即於中位下八十。以上一呼下一,一一如一,即於中位下一。上下位俱收,中位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。」
她唸完一般,驀然停下,緊揪著小眉頭。
奇怪,明明上頭每個字她都認得,可湊在一起,她卻一句也看不懂。
她不甘心的盯著重複一看再看,看了好久好久,久到兩粒眼珠子都鬥在一起了,卻還是有看沒有懂,這才死效起頭,悶聲問。
「什麼意思啊?」
終於,年歲稍大的男孩抬起了眼,看著那才六歲大的女娃兒,她支在桌上,小小的手捧著自個兒嫩肥的腮幫子,一雙黑瞳咕溜溜的,滿是好奇和困惑。
「這是乘法。」他提起了筆,拿了張宣紙,邊說邊寫,示範給她看一遍。
她歪著頭,在他的解說下,恍然大悟,但仍忍不住問,「這可以幹嘛?」
「算帳。」知道她得不到答案不會死心,他瞧著她,把一旁的桂花甜糕整盤拉過來,說:「這一盤裡有幾塊甜糕?」
她看一眼,笑道:「六塊啊。」
「給你五盤同樣數量叼糕,你會有多少甜糕?」
「等等、等等,我知道。」她抬起十根手指數半天,自己的不夠還借他的來數,可就算加上他的也不夠,她還又加了自個兒的腳趾頭才終於算出來,不禁得意洋洋的道:「三十塊,這樣我會有三十塊甜糕。」
「如果是二十盤呢?」
「咦?」她瞪著他,一時驚慌了起來,脫口抗議:「這樣不夠算啦!」
「是一百二十塊。」他眼也不眨的說。
她瞪大了眼,不敢相信的問:「騙人?為什麼?你怎麼知道?」
這丫頭的表情如此誇張,讓他眼中渾現笑意,繼續道:「三十盤是一百八十塊,四十盤是二百四十塊。五十盤是三百塊。若是有三百塊甜糕,咱們鳳凰樓裡就人人都能分得一塊甜糕。」
她張口結舌的,滿臉的驚詫與佩服。
「為什麼你不用數就知道有多少?」
他輕點了眼前的書冊兩下,「這是乘法,書上教的。三加三得六,你知道吧?」
「嗯嗯。」她用力點點頭。
「但若是三乘三就得九,是三與三相加三次。你算算看。」
她很快數了一下自己的指頭,驚訝的道:「真的耶。」
「把孫子算經學會,習得其中乘除之法,你就能像我一樣,很快便知道能得幾塊甜糕。」
她杏眼圓睜,大為驚奇的問:「真的嗎?」
「真的。」他點頭。
「整冊書習會就能知道?」她大大的眼,發出了亮光。
「整冊書習會就能知道。」他告訴她:「咱們鳳凰樓裡的管事,人人都得先習得此書。老爺說,若習得了這冊書,就讓我到店舖子裡去幫忙。」
聽到這裡,她興奮的扯著他的衣袖,「那你教我,快點快點,教我。我也要去店舖子裡玩。」
他到店舖子裡,不是去玩的,可看她這麼熱切,他沒多說什麼,只點頭應了她。
原以為,她只是一時好玩。
孫子算經,豈是她這樣小的娃兒就能通曉。
怎知那日之後,她日日捧著那冊書,去哪兒也帶著,嘴裡時不時就搖頭晃腦叨念背誦個兩句,整日埋首那算經中,非但抱著那算經上床,就連飯都能忘了吃,當然更別提其他。
這丫頭一入迷總顧不得旁,偏生她又愛黏著他,任何娘丫鬟都不要,教別人顧著,她總也得溜個不見蹤影,然後遇到了問題,三不五時就跑來找他,有時甚至就窩在他床上。
一日兩日,他還無所謂,到得三四日、五六日,她頭上的雙髻早散亂,身上也發出臭酸味,他才發現她根本沒洗澡,只得拖著她到浴池洗澡。
「不要、不要,我不要——」
「什麼不要,你臭了。」
「才不臭啦!我洗過了啦!」
「假裝用水沾沾手不叫洗澡,那連洗手都不是,你聞起來都像臭掉的優酪乳了。」
「呀,等一下、等一下啦,我等一下會洗啦——啊——」
即便她七手八腳死命的抵抗,一路哇哇怪叫,他還是成功將她拖到了浴池旁,剝了她皺成梅乾菜的衣裳,將她扔進水裡,像洗小貓般,將她從頭到尾刷洗得乾乾淨淨。
到了一半,興許是因為都已經整個人泡在水裡了,她才不再掙扎,卻氣嘟嘟的紅著眼,撇過臉去不理他。
他不管她,逕自替她把長發也洗了,但洗完之後,她卻還是倔強的不肯和他說話,泛紅的眼角,還盈著淚光。
「哭什麼?」
「哼。」她扁著小嘴,把臉撇到另一邊,淚水卻因此飛了出來,叮叮咚咚的落在水中。
這下子,讓他更不爽快了,一股氣哽在胸口,上不上,下不下的,只得將她從池子裡拖了上來,拿著布巾粗魯墊她擦乾,邊兇狠的道:「愛哭鬼,不過是洗個澡而已,有什麼好哭的啦!師叔說過,不洗澡容易生病啊!」
此話一出,只讓她哇的一聲哭了出來,委屈又氣惱的喊:「可是,你害人家的書都濕了啊——」
他一怔,朝她所指的地方看去,才看見那本他給她的孫子算經,早已濕透泡開,搖搖晃晃的浮在水中,正緩緩下沉。
「我、我明明有叫你等一下的……」她皺著小臉,邊哭邊抱怨道:「可你都不聽……」
他訥訥無言,好半晌,只能道:「只是一本書而已。」
「可那……」她皺著臉,扁著嘴,抽噎著說:「那是阿靜給我的啊……」
這一句,讓他愣了一下,只能瞧著眼前那小小的娃兒。
她小小的臉蛋漲得通紅,哭得一把鼻涕、一把眼淚的,豆大的淚一直掉,不知怎,竟比先前更加讓他難受得緊。
「對不起……你別哭……別哭了啦……」聽得自己的聲音,他才發現自己已拿布巾替她拭去臉上的淚,悄聲承諾:「我再抄一本給你。」
這一句,讓她瞬間哭聲稍歇,睜開水漾般的大眼,狐疑的瞅著他。
「真的?」
他一定會後悔的,那瞬間他不是沒想過,可一張嘴,卻還是無法控制的冒出了保證。
「嗯,真的。」
確定他是說真的,她原本還哭得像肉包子一樣皺皺的小臉,霎時破涕為笑。
那笑靨,好可愛、好可愛,像春天裡陽光下迎風搖曳的小花一般——
但,那才是惡夢的開始。
自此而後,她背誦算經的聲音,就理所當然的不斷迴蕩在他耳中,整整個把月,未曾停過。
「凡算之法,先識其位,一從十橫,百立千僵,千十相望,萬百相當……」
她早也背,晚也背。
吃飯也唸著,洗澡也不忘,就連睡著了,都要夢囈個幾句。
「凡乘之浩:重置其位,上下相觀,頭位有十……六噗唧、五噗唧……」
三更半夜,他半夢半醒,只聽她嘟嘟囔囔還背錯,忍不住開口糾正:「是六不積,五不只。」
話出口,他猛然驚醒,才發現自己說了什麼,還在驚慌自己竟被制約,就聽見她咕噥道歉。
「對不起啦,是六不積,五不積。不對,是五六隻。咦?奇怪,是五隻還是六隻?」
瞧著她在夢中喃喃自語,困惑的攢著小小的眉頭的模樣,實在教人雄又好笑,他忍俊不住笑了出來,知道她沒繼續下去就無法睡好,只得嘆了口氣,認命開口提醒:「六不積,五不只。上下相乘,至盡則已。」
聽到了答案,她露出豁然開朗的笑容,翻個身窩到他懷中,又繼續嘟嘟囔囔。
男孩好氣又好笑稻了口氣,知道在她背完之前,他是不用想睡了。
明明和她說過了,這得活念不是死背,可她性子硬,偏是要先背起來再說。
天知道,這還只是捲上而已,還有卷中和卷下呢。
他的苦日子,恐怕才剛剛要開始而已……
水波蕩漾……
氤氳的水氣中,一位穿著僕傭衣裳的姑娘推開了門,端著一盤澡豆,朝那裸身在浴池中沐浴的男人走來。
她在他腦袋後方蹲跪下來,輕輕的把漆盤擱在地上。
男人沒有動,看起來幾乎像是睡著了,束起的長發依然是束起的,像是髒掉的麻繩一般,擱在腦後地上,灰灰髒髒的。
倒是他還記得要先洗澡再下水,清水在他矯健黝黑的皮膚上蕩漾,那模樣頗為誘人,可這兒燈火昏黃,再更下去就看不清楚了,實在有點可惜。
這一趟,他出門忙了個把月,若換做城裡其他那些二世祖,定是先把事交代給下人,就先回家梳洗休息,至少先吃飽喝足了,其他事改明兒再說。
可他不是,他就是非得要做到日落西山、三更半夜了,才願意回來。
明明這鳳凰樓又不是沒人了,也不差他一個。
瞧給累的,睡著了吧?發都還沒洗呢。
姑娘不以為然的撇了撇嘴,暗暗在心裡哼了一聲,但還是伸出手,小心翼翼的解開了他束起的長發——
驀地,原本擱在水中的大手,霍然抬起,閃電船抓住了她的手。
她輕抽口氣,抬眼瞧去,卻見他臉上的布巾還遮著他的視線,但他的大手確實準確無誤的逮住了她。
「你在這做什麼?」
低沉的聲音迴蕩一室,帶著微微的惱,質問她。
「替你送澡豆啊。」她眼也不眨,笑盈盈的說:「你出門那麼久,發一定久沒洗了,又髒又臭的,不多拿幾個澡豆來怎能洗得乾淨?」
「這是下人的事。」
「晚了,我讓大夥都去睡了,誰要你這麼遲才回來。」
他緊抿著唇,握著她手腕的手,略微收緊了一些,然後鬆了開來,作勢要起身,她瞧見忙迅速伸手壓住他厚實的肩脖,開口用最直接有效的話,阻止他。
「你別起來,一起來就什麼都讓我看光了,我還沒出嫁呢。」
這一句制止了他的動作,但讓他的下顎繃得更緊了,「你還想嫁,就不該在這。」
瞧他不開心的,可他的不開心,恰恰好就是她的開心呢,這幾年更是如此。
她嘴角噙著笑,收回在他肩上的手,道:「靜哥,我們是兄妹,妹子幫辛苦工作回家的兄長洗洗頭,不也挺應該的?躺著吧,我替你把發洗一洗。」
沒來由的,她那聲刺耳的稱呼竟較以往更加擾人。
「我可以自己洗。」他著惱的說:「你是大小姐,這不是你該做的事。」
她聽了,也不惱,只顧著解開他的辮子,笑咪咪的道:「你不把我當妹子你就起來吧。」
他全身肌肉微微繃緊,室內只有淙淙的水聲。
有那麼一秒,她以為他會站起,她屏住了氣息,等著。
但他沒有,終究是沒有。
看著他卻不動的雙肩,她心底渾現一絲惱怒,一點遺憾,可即便如此,她依然慢慢以指替他梳開了發,一次又一次,輕柔的、細心的,將他的黑髮梳開,拿木勺舀水淋濕,用澡豆在手裡打出泡沫,再抹上他的黑髮,按摩著他的頭皮。
剛開始,他依然有些僵硬,但緩緩的,她可以看見他放鬆了下來。
他這一趟跑船,去了益州將近一個月,她知道他已經比一般男人都還要愛洗澡了,可手上潔白的泡沫,依然漸漸染上了髒污。
就算在船上,也不是天天都有淡水可用,雖然說旁邊就是大江大河,總也不能要他天天生河裡跳,不是說他不想,這些年來兩人一塊兒長大,她曉得,他想得可厲害了,若不是因為礙於風家大少爺的身份,他定是天天往水裡鑽。
就沒見過哪個男人,像他這麼愛洗澡的。
所以,每次他一回來,她知道他一定是先到浴池裡泡上大半天,這是他少數縱容自己的奢侈。
這男人頂著的頭銜,明明就是風家大少爺,他平常卻處處苛待自己,無論吃的用的,他總是隨隨便便,除非是為了要和人談生意,衣著打扮得上得了檯面,否則他能省則省,絕不多花家裡一分一毫。
她拿起木勺,再舀起幾勺溫熱的水,替他沖洗長發,然後再上了一次皂。
他那雙黑亮的眼,仍置在布巾之下,但她看見,他額上的,已然漸漸撫平。
當她再次替他沖水,他的呼吸平穩深沉,一勺又一勺的,她讓水流將髒污帶走,小心的不驚擾他,讓那一頭長發再次變得烏黑柔亮,輕輕的她以小手覆上他的額發,避免水流衝入他的眼耳。
木勺裡的清水流盡,她的手指順著他的眉骨滑過,抹去那殘留的水珠,然後不自覺的停在那裡。
最後一道糾結在他眉間額上的青筋,在她溫柔的指尖下化開。
她能感覺,他溫熱皮膚下的脈動,那麼穩,那般沉,就像他的呼吸一般。
睡著了嗎?
不由自主的,她彎下身來盯著他黝黑的面容。
他的嘴角下巴,經過了一整天,已冒出了些許胡碴,滴滴的汗水從毛孔中滲了出來,懸在其上,然後順著他臉上嚴酷的線條,匯聚滑落。
左邊的眼角旁,有些新增的扭曲小疤痕,看起來像是燒燙傷,但已經好得差不多了,它們不是很顯眼,不仔細看還不會看見。
可她向來很注意他。
這實在不是一個好習慣,但她改不掉。
他有一張很好看的臉,不是那麼俊美,但很方正,很男人。
她記得他兒時的模樣,他有一張老臉,當時他就和爹那種俊美的模樣有很大的落差,成年之後,他的樣貌和爹差更多了。
少年時,他有陣子突然抽高拉長,她曾聽過人們在背後說他醜,好像穿著人皮的骷髏一般,夜裡瞧了都要嚇出三魂七魄來,但成年之後,他的臉與身上都長了肉,變得十分強壯,他還是不好看,沒爹那麼好看,但嫌他醜的人少了,倒是許多丫鬟看見他,會羞得臉紅續。
從小,她總追著他的腳步,跟前跟後的。
他一直都在她身邊,她也一直崇拜著他。
直到某一年,她發現他不知怎地開始消失了,不再牽著她的手,不再任她隨傳隨到,不再注意看著她,不再是理所當然。
然後她才驚覺,他長大了,成人了。
他不再是個孩子,也不再是青澀少年,他變成了——
一個男人。
驀地,一隻濕淋淋的大手抓握了自己的手腕,她才發現,她的手指不知何時,竟溜到了他唇邊。
「鬍子長出來了。」她鎮定的說:「我替你剃了吧?」
他的喉結上下滑動了一下,然後張開了嘴。
「不用了,反正明早還要再剃一次。」
他低啞的嗓音,淡淡迴蕩在浴室之中。
這一回,她沒和他爭辯,即便她臉沒紅、氣沒喘,聲也很穩,卻無法隱瞞她腕上太過急促的脈動。
「也是。」
匆匆的,她抽回了手,拿來一旁乾爽的布巾,包住了他濕透的發,邊佯裝無事,冷靜的道:「乾淨的衣裳都給你放在架子上了,起來記得把身體擦乾再出去,你別又在這兒睡著了,皮都泡皺了。我在你房裡備了宵夜,一會兒吃些就早點歇息了吧。」
說著,她緩緩站起身,收拾了他的髒衣物就往外走,臨到門前,又忍不住停步回首。
「浴池現在是二楞子負責整理的,他明早上自會來打掃,你別搶他工作,他會哭的。」
他沒有答應,只是保持著原來的姿勢,慵懶當在氤氳的熱水裡,臉上還蓋著那條布巾,看起來該死的性感,該死的可惡。
可她知道他聽見了,二楞子幼時燒壞了腦袋,整個人傻傻的,被搶了工作是真的會哭的,她清楚他不會多事。
所以,她沒敢再看那個泡在浴池裡的裸男一眼,怕自己會忍不住回到他身邊,撇開他那死命蓋在臉上的布巾,做出些什麼蠢事。
匆匆的,她推門走了出去,關上了門。
夜涼如水,她快步走在沁涼的月夜之下,依然感覺心頭狂跳。
她一路走回自個兒房裡,直到回到房了,坐下來了,才發現手中仍抱著他的髒衣裳。
她完全忘了要先將它們拿去洗衣房,到此時,紅霞才無法克制的上了小臉。
「可惡。」她輕咒一聲,原本想將那滿是他汗臭味的衣裳扔到地上,可半晌過去,她卻依然將那臭衣裳緊握在手中,而且還不小心發現他的褲腳都是干掉的泥水,手肘與膝頭的地方,也磨損得差不多了。
該死的,這哪像個大爺的行頭,怎麼看都像港口碼頭上那些苦力穿的,真是教她看了就一肚子火!
這些年,那死心眼的男人只花自己領的薪餉。
三年前,當她在帳簿上發現他給自己發餉,而且竟然只領和一般小掌櫃一樣的薪餉時,她真是氣得眼前一片花白。
裝什麼清高啊!王八蛋!
看著那又髒又臭,幾乎快破掉的衣褲,想也沒想的,她伸手扯破了它,那並不難,它本來就磨損得能透光了。
「唉呀,真糟糕,破了呢。」
瞧著那可以穿過整個拳頭的破洞,她一點也不真心的說著遺憾的話,一邊繼續搞破壞,直到那套衣服被她弄得七零八落,不成樣了,她這才把整套衣裳都扔了,上床去睡覺。
「你說什麼?!有膽再說一次!」
「我就說!我就說!我說你家那少爺才不是少爺,他是個假貨,你娘生不出兒子來,你爹才撿他回來的,他爹娘不要他,就鳳凰樓拿他當個寶——」
「你這王八蛋!看我揍死你!我叫你說!叫你說——」
「啊——好痛、好痛!你這瘋婆子!快放手!放開我——爹、娘——哇啊——」
遠遠的,才剛滿十四的少年,就瞧見了那丫頭,騎在一個被撲倒在河岸邊的男孩身上,她攥緊著拳頭,發了瘋似的,一拳一拳就往那少說大她兩歲的男孩身上打。
他腳一點地,施展輕功,迅速上前,攔腰將那丫頭強行從被打得滿頭包的男孩身上抱開。
「做什麼?放開我!」她生氣的大喊著,回頭見是他,也不熄火,只嚷嚷著:「阿靜,你放開我!我要捧扁他!」
少年當然沒有聽她的,反而是死死鉗抱著像蟲子般奮力扭動掙扎的丫頭,往後再退一步。
「你不能捧扁他。」他冷靜的勸說:「當街鬥毆是要抓去衙門裡打屁股四十下的,你忘了嗎?」
上個月,他確實很鉅細靡遺的清楚解程過笞刑這件事,所以聽他提起,她稍微冷靜了一點,但仍有些憤憤不平,生氣的吼著。
「可是,是那頭蠢豬先惹我的——」
那男孩聽了,雖然已經被揍得鼻青臉腫了,還不知死活爬起來哭著沖道:「我又沒說錯!這個醜八怪本來就是撿來的!」
「你還說,看我撕爛你那張臭嘴——」
原本才稍稍安分下來的丫頭,瞬間又扭動掙紮起來,兇狠的伸出手,對著那傢伙張牙舞爪的,試圖再次毆打他。
「銀光,住手!」
雖然少年依然抱著她的腰,再次往後退帶她遠離那男孩,但她滑溜得像條魚一樣,混亂之中,竟還真的讓她又對男孩踹出了一腳。
砰的一下,她的腳丫子,硬生生踢到了男孩的口鼻,男孩被踢得揚起了胖臉,剎那間,鮮紅的鼻血與一顆白晃晃的牙頓時在空中齊飛。
「嗚啊——我的牙、我的牙——嗚嗚——你這個瘋子、瘋子——」男孩捂著噎血的口鼻,嚇得撥腿就跑,卻還是不斷頻頻回頭對著她又哭又罵。
「王八蛋!你好膽別走!阿靜!你放開我、放開我啊!讓我給他好看——」
她火冒三丈的叫囂抗議著,但身材已經抽高拉長,逐漸變得強壯的少年當然不曾鬆手,他將那氣瘋的小妮子扛上了肩,迅速帶她離開犯罪現聲。
一路上,也不顧旁人側目,她依舊不斷在他肩頭上叫囂掙扎,好不容易到了家、進了房,當他將她放下來時,她頭上的雙髻理所當然的又散了,腳上的鞋掉了,身上的衣也歪了,整個人披頭散髮的,一張小臉氣得紅通通,鼓脹得像海裡的河豚一樣。
她一下地,立刻氣呼呼的轉過身去,不肯看他。
瞧她那模樣,只讓他好氣又好笑,但更多的,卻是熨上心頭的暖。
她這陣子到處惹是生非,幾乎揍遍十里長街的半數孩子,可他知道,她生事的原因,幾乎都是為了他。
他耳朵太好,總是將該聽的,不該聽的,都聽入了耳。
應該要責怪她的,可到頭來,當他伸出了手,卻只是拿了木梳,替那和他生悶氣的丫頭,重新梳髮弄髻。
她原先因為賭氣還想閃,但猶疑了一下,最後還是乖乖站在原地,讓他替她整理長發。
這野丫頭,三不五時就會把自己弄得亂七八糟,因為老爺身體不好,夫人時常顧不到她身上,他逼不得已,只好隨身帶著髮梳,養成了替她整理的習慣。
她的發,長到了腳邊,卻總是讓她自個兒弄得糾纏成一團。
他耐心墊她把打了好幾個結的長發梳開,一邊卻又忍不住好笑的低斥:「小瘋婆子。」
她忍耐的沉默了好一會兒,最後還是不禁咕噥抗議:「我才不是。」
對這抗議,他沒再多做評論,只是笑意卻無法抗拒的上了嘴角。
他熟練的幫她重新紮好雙髻,淡淡道:「你不能毆打所有說我閒話的人。」
她僵住了,動也不動的。
他猜她以為他一直不知道她為什麼打架,她從來不曾說過原園。
「如果真的忍不住,下次揍肚子就好。不要打臉,打臉太明顯了。」他說。
她再一愣,整個人轉了過來,傻眼瞪著他。
「還有,記得找沒人看到的地方,才不會被抓到。」他替她把前面的瀏海梳整齊,道:「但直接打人還是最笨的,因為那很容易被發現,最好的方法,是暗地裡給他好看。」
她杏眼圓睜,好奇的問:「怎麼做?」
「收購他家的店舖子,讓他叫你小姐。」
他瞧著那可愛又暴力的小瘋婆子,將歪斜的衣裳拉正,替她重新綁過一次腰帶,道:「把你的敵人,變成朋友,然後他就不敢再說閒話了,至少不敢公開的講。」
她擰著秀氣的眉,道:「我也不喜歡他們私底下亂講。」
心頭,莫名的再一揪。
凝望著眼前頑固的丫頭,她烏黑的大眼,如此坦然而直接,他喉頭著,然後蹲下了身,幫她拉好鬆脫的羅襪。
「阿靜?」
「嗯。」
「為什麼你叫爹娘是叫老爺夫人?」
他略略一僵,看著她套著白色羅襪的小小腳丫,半晌,才道:「我是風家少爺。」
這不是一個回答,它沒有解決她的疑惑。
她困惑的看著低著頭,從一旁衣箱裡替她拿出另一雙新鞋的他,悄聲再問。
「你是我兄長嗎?」
這個問題,讓他又僵住了,但只有一下下,他把小小的新鞋,套在她腳上,先是左腳,然後是右腳。
她等著他回答,可他始終沒有開口。
莫名的,她不安了起來,當他替她穿好鞋襪時,她叫住了他。
「阿靜。」
終於,蹲在身前的少年,抬起了眼。
她認真且執著的看著他道:「你不要擔心,等我長大之後,我就嫁給你,這樣就不會再有人說閒話了。」
眼前小小的姑娘,眉潔目秀,衣著端莊,一左一右頂著兩個小小的發髻,她看起來,就像個可愛的三彩瓷娃娃,可和其不同的,是她小小的臉蛋上,有著因為激動而泛起的嫩紅,一雙烏黑的瞳眸閃著堅定的亮光。
她是認真的,非是妄言,不是虛語。
他無言以對,只聽到心在跳。
待回神,他已伸出雙手溫柔的將這可愛的女娃擁在懷中,抱著她起身,往外走去。
「阿靜,你有沒有聽到?」她圈著他的頸項,乖乖的讓他抱著,卻依然忍不住叨絮,「等我長大嫁給你,你就什麼都不用擔心了。」
他沒有回答,只是像捧著剛出爐的瓷娃娃那船,小心翼翼的捧抱著懷中的小女娃,穿過長廊綠柳下,送她去陪她爹娘用膳。
可她不甘心沒得到回答,仍是執著的在他耳畔,一問再問。
「阿靜,你聽到了沒啊?聽到了沒啊?」
是聽到了沒啊?
她翻身掉下床時,彷彿還聽見自己稚嫩的聲音在室內迴響。
「可惡。」
姿勢難看的趴在地上,她萬分不變的咒罵出聲。
都是他害的!
事後回想起來,她小時候問他這個問題的時候,他從來不曾回答過。
每次她說她要嫁給他,他不是顧左右而言他,要不就乾脆假裝沒聽到。
那麼多年來,她還以為他的心會在這裡,就算不在她身上,也在風家,在鳳凰樓上。
她以為他就算不在乎人,至少在乎這些年他打下來的江山。
可直到三年前,看見他發給自己的薪餉,她才知道,他從來不曾想要留下。
他不擔當風家大少爺,不希罕富甲天下的鳳凰樓,他會在這裡,只是因為他認為他欠了爹娘一條命而已。
他是個棄嬰,是養子,他和她不是親兄妹,從來就不是。
他顧著她,護著她,然後突然有一天,他就出門去了,一次又一次,回來了又出去,回來了再出去,從此再也沒有停止過。
她都已經習慣睡他床上了啊,習慣床邊會有他擋著當欄杆,習慣他替她梳髮整衣,習慣一伸手就能抓住他,可他縱容著她養成一堆壞習慣之後,就拍拍屁股走人了,留她自己一個人收給善後。
都是他害的!
可惡可惡可惡——
生氣的捶了地板好幾下,她這才爬坐起來。
窗外,天還是黑的,好黑好黑。
她曲起膝頭,把腦袋擱在上頭,只覺眼眶發酸。
都是他害的……
發燒鑑貨團  |
每天精心挑 選的優惠 |
特價下殺的 數位相機及攝影機 | 精品/手錶 / 品牌旗艦 |
| 居家生活 | 交通/美食 | 視聽家電 | 禮物與飾品 |
| 美妝保養 | 電腦資訊與 消費電子 | 好書共享/熱 門書籍 | 服裝鞋包配 飾 |
| 小遊戲分享 快來打發時間吧 | 集點王介紹 、教學、問與答 | 通路王介紹 | |

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